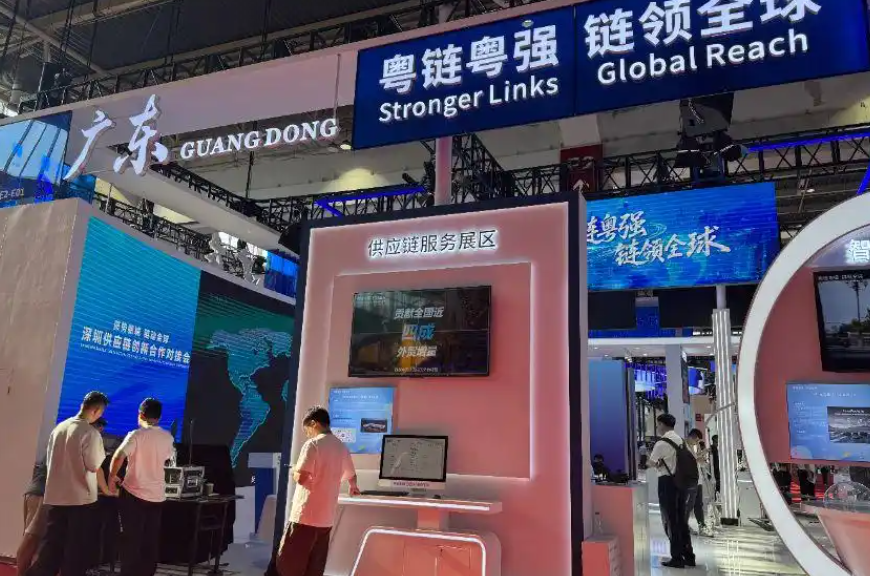摄影师记录藏区同胞十年的生活变迁
看中华 最新资讯 2015-11-27 09:01:03

2005年5月2日10点43分,星期一,代吉和弟弟妹妹们在海拔4000多米的山坡上匍匐前行采挖虫草,每天都要在潮湿的草甸上爬来爬去,时间长了手和膝盖都会疼痛。原本该坐在教室里上课的他们,每年5月至6月这段时间都不能去学校,尽管老师们挨家挨户地喊这些孩子到校读书,但最终都无功而返。据当地虫草区的商贩们介绍,从80年代中药市场放开后,藏区冬虫夏草的价格逐年涨价,截至2004年年底,每公斤冬虫夏草的平均价格高达8万元。图文:感恩中国网站张仁杰

2005年5月7日18点03分,三步一跪磕长头的达杰才仁打算停下来在路边休息了。据达杰才仁告知,他是2004年5月份开始从老家出发的,每天磕长头的时间都不会少于8个小时。为了这次朝拜,他卖光了家中所有可以变卖的东西,和弟弟一起开始了朝拜之路。他的弟弟负责在前方拖着板车拉运他们的行李,行李也极其简单:衣物、帐篷、锅碗和简单的食物。他也坦言整整一年时间的磕长头让他身体的关节严重受伤,特别是双膝,每次下跪的时候都疼痛不已。按照他的朝拜路线,他可能还需要两年的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在路上的达杰才仁把生死看得很淡,如果死在路上也值得了,但只要他还活着,就一定会遵从佛陀的教诲,摆脱轮回之苦,修成佛道,祈愿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

2006年4月28日6点46分,已经怀孕5个月的巴毛很吃力地用竹篓把自家门前的雪背到外面去,她已是五个孩子的妈妈了,在她家门口不远处的土墙上醒目地写着:“自愿少生一个孩子,政府奖励3000元。”巴毛不认识汉字,她也明白孩子生多了女人受累,可她也无法控制自己的肚子,怀上了就必须要生,她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自己不再生孩子。在当地,居民们都信仰佛教,信佛的居民们绝不接受堕胎,他们认为,堕胎就是杀生,是重罪,不仅会下地狱,而且活着的时候也会倒霉一生。

2006年5月6日15点02分,东周和他的爱人忙着用马车运送修建房屋的泥土,由于当地还没有通乡公路,居民大都以牛马为交通工具。这里属于农业区,祖辈们以种地为生,但随着近年虫草价格上涨,挖虫草逐渐成为当地居民主要的收入来源,种地反而成了副业。农业区周围的山上很少有虫草出现,只有小部分区域的山上才可以采挖到优质虫草。为了采挖虫草,他们不惜每人每年要花1000多元来办理虫草采挖证。现在正是上山采挖虫草的季节,可是东周两口子并没有上山,东周的眼睛不好,一天下来有时候连一根虫草都挖不到,而他的老婆怀孕7个月了,也无法弯腰爬行挖虫草。

2007年4月29日11点06分,四朗多吉正带着亲人们耕种土地。虽然当地山大,但是可耕种土地面积很少,当地的高寒气候也直接导致庄稼产量不高,加上他们对洪水和干旱之类的灾害也无能为力,一般情况下只能求助于神佛,耕地收入十分微薄。四朗多吉打算耕种完土地后就到城市打零工挣钱,他的这个想法在村里属于超前的。村里的部分居民,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一辈子都没去过当地的县城,老人们的想法很简单,城里没有土地可种,自己也不认识汉字,到城里吃啥?

2007年6月5日15点49分,三布罗和他的爱人站在公路旁叫卖新鲜虫草,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摆脱虫草商贩压价,想把虫草的价格再卖高一点儿,当然,他这样做也面临着被虫草商贩打骂的风险。今年的虫草价格创造了历史新高,每公斤的价格已经上升至19万元左右。虫草价格的快速上涨,也让居住在原本无工业,也无商业的高原虫草区居民们看到了发财的机会,除了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婴幼儿,能上山的都上山了。然而,虫草价格上涨并没有给当地居民带来更多的收入,购买虫草采挖证的费用增加,采挖人数的大量增加、虫草的日益减少也让虫草区的居民们收入减少,甚至有些居民们不仅没有挖到虫草还倒贴购买虫草采挖证的费用。

2007年6月13日17点51分,扎西让布和家人们一起把满满一车生活垃圾丢到东俄罗理渠河内,垃圾中的塑料方便袋占据了一定的份量。当然,这样的情景在当地不属于个案,集镇上的居民大都会把各自的生活垃圾倒进河内,垃圾多了,河道里臭气熏天,发黑的河水里连鱼虾都极其难见,高原农村和内地农村同样遭受着大面积的垃圾污染。

2007年9月8日8点18分,13岁的措毛在大人们的带领下把牧场的牛粪收集到一起,然后用双手把牛粪涂抹在草甸上晒开。牛粪是牧区的主要燃料之一。措毛和她的亲人们常年生活在边远牧区,没有学校,没有医院,没有集镇,没有电,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牧区的女人们承担了大部分的劳动,不仅要养育后代,还要上山放牧,包括端茶做饭的家务事也基本上都是女人们在做,而她们却很少抱怨,除了牧场周围外,她们几乎不去其他的地方。

2008年6月25日10点43分,9岁的才旺求周在教室里充当临时老师。他所在的村小就读学生不足30人,全校只有一名代课教师,一个班级。遇到代课老师因事不能来学校上课的时候,才旺求周就当起了小老师。受当地宗教影响,当地有部分就读小学的孩子们会在中途或者适龄读书阶段就到寺庙出家为僧,这也是让当地教师最为头疼的事情。另一方面,乡村学校硬件落后、师资匮乏等因素,也影响到家长让子女读书的积极性。

2008年7月8日7点30分,伦珠和他的工友们一早就赶到寺庙工地,开始打磨石块。他老家的海拔1800米左右,为了挣钱,他跑到海拔大概在4000米左右的高原工作,虽然他在这里修建寺庙已经有十一年的时间了,脸上的肤色已经晒得和当地人基本一样,但他还是不适应,高海拔导致的缺氧让他吃不好睡不香。伦珠虽然是专门修建寺院的,但他认为寺院修建太多不是好事。按照常理,寺院多活佛多是件好事,可以为当地人更多地主持佛事,并为当地修行人提供教导和支持。可实际上并非如此,活佛们都很忙,忙着去做到内地招收新弟子、筹集善款修建寺庙这一类的外事活动。活佛都外出了,寺院无活佛成为常态,进而会导致部分信徒,特别是青年一代宗教意识淡化。

2008年7月9日9点02分,72岁的扎西才措老人用手轻轻抚摸着生病的小牦牛,她所养的小牦牛应该属于典型的包虫病症状,该病是寄生于人或动物体内的慢性寄生虫病,可以在牛羊、犬类动物及人类间传播,一旦感染包虫病,人类和动物的死亡率都很高,因该病导致的农牧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十分突出。游牧居民最大的特征就是居住比较分散,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几乎与现代文明隔绝,他们的子女接受教育的机会很少,文盲率较高。牧区位置的偏远和封闭造成了医疗和防疫的严重滞后,像扎西才措这样的牧区老人还有许多,她们一辈子都生活在牧区,外面的世界几乎与她无关,甚至一辈子都没有去过县城一次。

2009年6月26日17点51分,满身灰尘的尼玛旺索正在雕刻玛尼石,为了学会这门手艺,他已经跟着师傅学习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由于这种手艺属于高原藏区的专利,他打算出师后和师傅一样依靠雕刻玛尼石为生。不过,私底下他表示,他不喜欢这门手艺,雕刻过程中的灰尘太大,他的师傅因为吸了太多灰尘导致现在呼吸困难。虽然尼玛旺索有意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但他很迷茫,不懂汉语,没有文化,没有技术的他还能干什么?

2009年7月16日15点00分,在尼姑寺出家的多杰桑毛在房屋前席地而坐,她的左手拿着小木棍在泥土地上来回划着圈圈。她三岁不到就被父母送到寺庙出家为尼,前后闭关两次,每次三年。虽然她已经闭关结束,可以下山到集镇上走走,但她的上师不允许她们四处走动,走得多了,看得多了,容易被外面的物质世界感染,就不会安心念经修行了。像多杰桑毛这样出家为尼的女孩还有许多,在当地,如果家里有两个以上的子女,家长会考虑让其中的一个子女到寺院出家修行,他们认为,出家为僧,功德无量。

2010年4月16日13点42分,丁增南加和寺院里的僧人们花费5个多小时从倒塌的废墟里扒出一具遇难者遗体,他们找来一床棉被把遗体包裹好,小心翼翼地抬出废墟,他说,这也是留给死者最后的尊严。丁增南加不是玉树本地僧人,“4·14玉树地震”发生后,丁增南加和寺院里的僧人们一起租了一辆面包车赶赴一千公里之外的地震灾区参加救援。本次7.1级地震共有2698人遇难。

2010年4月20日13点41分,风沙特别大,19岁的俄金卓玛和哥哥姐姐们依旧在公路上叩首朝拜前往拉萨。“4·14玉树地震”中她的双腿受了伤,走路都有些艰难,考虑到她的腿还没有康复,这次朝拜家人原本打算不带她的,毕竟从玉树朝拜到拉萨最快也需要大半年的时间。可是她说什么都要一起去,就是爬也要爬到拉萨去,她希望通过发愿叩首朝拜来祈求佛祖护佑活着的人们幸福平安,保佑受伤的同胞早日康复,希望地震中不幸遇难的同胞们都能早升极乐。

2010年7月13日10点32分,永丁江措和他的邻居们赶着各自家的牦牛前往寺院,眼下的牛羊也是肥壮季节,这些牛羊也是他的父辈们辛苦放牧所得,按照内地人的说法,也是他们一辈子省吃俭用留下来的家产。他们要把这些牦牛贡献给寺院里的活佛,寺庙里的管家也在几天前找到了买家,等他们把牦牛贡献给活佛后,管家就一次性出售给买家。在当地,给活佛的经济供养仍然以实物为主,主要以牛羊和酥油为主,个人或家庭有事请求活佛时,无论给孩子起名、卜算、诵经都需要有一定的供养,数目从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往往是根据个人的经济条件和心意来决定。

2010年7月25日11点03分,62岁的旦真牵着他的骆驼坐在路上四处张望着,受玉树地震的影响,最近的游客比较少。旦真在景区周围做牵骆驼的生意已经有十多年了,刚开始的时候只拍照不骑骆驼不要钱,后来牵骆驼照相的人多了,就开始收钱了,现在拍照每人每次10元钱,如果想骑骆驼走沙漠,来回半个小时左右,每人每次100元。旦真是景区周围的农民,随着游客增多,他也不再种地了,完全靠牵骆驼为生。谈及当地旅游,旦真欲言又止,游客多了,骗子也多了,为了让游客多掏钱,各家旅行社打起了价格战,采取强制购物等手段挣钱。不仅如此,各路“神仙”也都出来了,算命大师、中医大师、风水大师之类的应有尽有。旦真也担心,再这样下去,上当的人多了,以后谁还敢来此地旅游?

2011年7月21日9点52分,虫草商贩更求罗周一大早就来到县城街道收购虫草,这段时间上山挖虫草的老乡们都下山了,不宽的县城街道挤满了买卖虫草的人。虫草价格连续上涨,让当地居民们和虫草商贩为之疯狂,如果想到虫草多的区域采挖,需要花费数千元购买虫草采挖证。每到采挖虫草的季节,附近的居民拖家带口,只要有力气爬山的人一般都带上帐篷和干粮上山开挖。更求罗周有些担心虫草价格无节制地上涨肯定会出现问题。如今当地居民收入过分依赖虫草,然而过度挖掘虫草会破坏高原脆弱的草原植被,使得草原沙漠化越发地严重,虫草的数量也越挖越少。假想一下,如果虫草没有了,当地居民的收入从何而来?没有了经济收入,以后的生活该怎么过?

2011年7月27日12点46分,西然卓玛和同学们坐在校园废弃的水池旁吃午饭。从下个学期开始,他们就读的村小就要合并到县城小学了,按理说是件好事,毕竟村级小学老师缺乏,配套设施跟不上,影响孩子们接受正常的教育。但让老师头痛的是,合并学校后,由于到校路途遥远,家长们只能依靠摩托车接送孩子,家长累,孩子也累,进而导致部分家长不支持孩子继续读书了。在当地,家长们不重视教育的原因很多,比如说,有部分家长开始时很重视孩子的教育,花费很大的人力和财力把子女送到学校,但孩子成绩却不太理想,绝大部分初中毕业就不再读书了。这部分孩子的眼界自然比文盲父辈们开阔了许多,起码会说汉语,但他们宁愿在街头游荡,也不愿意回到牧区放牧或者农村种地,这让部分家长怀疑自己当初的决定。

2011年7月29日12点19分,67岁的义西生格老人在佛塔前制作佛器。老人没上过学,在牧区生活了一辈子,如今年事已高。老人从去年5月份开始从牧区搬到山下的村庄居住,老人生活很有规律,吃饭、念经、转佛塔,每天如此。提起她的孙子们,老人有些不高兴,孙辈们每天都忙着外出做生意赚钱,忙得连念经的时间都快没有了,宗教意识和情感逐渐淡化。一边是传统的宗教文化,一边是现代化生活,这其中的心理矛盾不言而喻,物质追求重要还是精神追求重要?还是既要物质也要精神?这个问题让很多人困惑。

2012年7月16日16点17分,曲尼让姆和两个妹妹在青稞地里徒手拔除野草,下地干活儿已经成为当地女人们的专利。曲尼让姆居住的区域属于纯农业区,风调雨顺的情况下,依靠土地维持全家人的温饱应该没有问题,但想要有多余的钱用就没这么简单了。一直以来,藏区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央政策的倾斜和财政上的大力支持,但由于受制于当地的高原环境和人文环境,当地工业化进程相当缓慢,农牧业生产依然处于原始状态,所以当地部分青壮年也开始考虑到城镇或者内地打工赚钱。但受制于自身的语言差异、文化水平、生活方式、劳动技能等不利条件,其就业空间大大受限。

2012年7月19日17点51分,自愿到寺庙参加劳动的西然卓玛和同村邻居们紧张地劳动着,寺院活佛从大城市的弟子们那里筹集了一大笔善款,开始大动土木修建寺庙。与此相反的是,当地基础设施建设进展缓慢,乡镇医院乃至县城医院的环境远远落后于寺院,也有人建议当地的活佛少建几座寺院,多修建几所学校或者医院。对此,活佛们有自己的看法,医院也好,学校也罢,那是政府的事情,与寺院无关,能够筹集更多的善款把寺庙建得更辉煌,他的功德才更大。

2012年7月30日17点05分,54岁扎西平拉和爱人在刚刚耕种过的土地里清除杂草,他最小的女儿刚刚考取了内地的一所大学,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让他着急,依靠种地,绝对负担不起女儿在大学期间的各项费用。他的家坐落在著名的旅游风景区,他也尝试过在景区周围做小买卖,但最终还是亏本了。景区旅游业的兴旺和巨大的投资机会,使得大量内地的非藏族群体涌入景区寻求发展机会。由于资金、技术和知识水平的优势,他们在商业、服务业及旅游业等各领域都占尽先机,逐步成为藏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景区周边的农牧区不仅没有得到快速发展,反而被边缘化,当地居民的焦虑和不安情绪在增加。

2012年8月2日11点58分,次仁穷达用马车拉送油料,她在村里开了一间小商店,除了日用商品外,最好销售的就是汽油。曾经的游牧民族外出大都骑马,如今,马匹都被摩托车代替了,但摩托车造成的交通事故也越发严重。现在牧区或者乡镇及其县城,已经很少看见骑马行进的场景了。摩托车多了,汽油便成为紧俏商品,有关系的当地居民通过走后门的方式购买汽油,然后把汽油从很远的地方拉回家销售,虽然这些油的品质很差,且价格很高,但销路仍然很好。

2013年7月15日15点51分,边巴云旦和他的朋友忙着玩骰子游戏,边巴云旦的手气不好,输了一百多元钱,为了能把输掉的钱赢回来,他必须继续赌下去。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多,赌博在当地发展迅速,“钱多大赌,钱少小赌”的思想开始在青壮年间流传。饮酒、对歌和跳舞是当地居民闲暇时重要的娱乐活动。当地人,尤其是农村居民,他们喝的酒基本都是自家酿制的青稞酒,制作环境简陋,卫生条件也很差,虽然酒精度数低,但喝上两斤后,自然就醉了。如果年轻气盛的人喝多了,打架骂人的事情还是无法避免。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看中华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看中华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